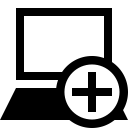目录:
视频: Ay shahenshah-e-madina assalat-o-wassalam | Kalaam e Jamil-e-Qadri | By Mohammad Sadiq Razvi (十一月 2024)

上周,一位同事收到了她两年前提交的一篇文章的打印机证明。 您没看错。 在获得硕士学位的那段时间里,她设法克服了学术同行评审的迷宫,从而发表了一篇论文。 如果您可以保持幽默感,那将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作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同行评审产生了严格,经过彻底审查的研究,可以改变领域的形态。 实际上,大多数期刊文章甚至都没有被引用,而且过程十分繁琐,特别是对于那些以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作为通用语言的初级学者而言。
不必一定是这种方式。 根据《 自然 》杂志,在科学领域,从接受到发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整个发表过程徘徊在100天左右。 许多科学家认为,这太长了。 科学迅速接受了一种称为开放式同行评议的方法,《 科学美国人 》将其简洁地定义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和审阅者的姓名彼此已知。”
尽管开放式同行评审不是万灵药,但没有理由让人道主义者无法使用它来使期刊出版更快,更友好,更轻松。
数字教育实验室(DPL)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替代方法。 它已有6年历史的在线期刊《 混合教育学 》( Hybrid Pedagogy )具有平流层的接受率,协作的开放式同行评审程序以及传统期刊难以理解的读者群。 但是请不要误会,DPL不仅挑战写作和编辑惯例。 它要求读者重新评估学术期刊应该做什么。 DPL嵌套在一系列其他宣传活动中,包括在线课程,播客,暑期运动学院,DPL致力于将学术期刊从知识库转变为调查社区。
回到学校
当我与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Jesse Stommel交谈时,他说编辑们总是将 混合教育学 作为一种杂志而不是学校。
Stommel解释说:“我不喜欢期刊文章是放在页面上并传递给受众的静态内容容器的想法。” “相反,我们一直试图做的是创建对话。这些文章成为创建对话和建立关系的一种机制。”
在最初的几年中,这些对话是通过日记进行的。 (该项目以Hybrid Pedagogy Inc.的名义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并不是偶然的。)但是,随着领导层开始进行公众宣传,尤其是通过DPL的暑期学院,这种平衡发生了变化。
现任编辑Chris Friend解释说:“当我们在2015年建立第一家DPL研究所时,那是该杂志的分支。”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意识到,地面研究所是我们想要与重要的数字教学法一起工作的核心和灵魂,该期刊成为DPL的分支。”
如今,关键的数字教学法遍及整个站点,其程度比该期刊的原始同名书更大。 我请圣利奥大学英语助理教授Friend解析这两个术语。 混合教育学认为,因为我们在数字和模拟环境中学习,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在虚拟与现实相交处工作的教学实践(教育学是幻想术语)。 同时,批判性的数字教学法提供了这种实践的理论:它将批判性的教学法(例如,Paulo Freire的 《被压迫 的 教育学》作为参考) 引入了与互联网的对话。
Stommel解释说:“我们的工作全部围绕实践,您不能将哲学和实践相距太远。” “我们将它们归入同一领域,因此,当您阅读 混合教育学 文章时,您会看到有关下一个事件的新闻;当您阅读事件时,您会看到我们的最新文章。持续的联系感:这些想法将这些事件变为现实。”
《 混合教育学 》杂志是DPL的使命和实践的中心。
对话从哪里开始
该期刊使用开放的同行评审过程,其作用不只是确定作者和审稿人。 在“ 混合教学法”中 ,编辑者 选择 他们认为最适合修订的审稿人,然后作者和审稿人直接参与。
他们的会议空间是文本,他们使用Google Docs的多线程边注实时进行讨论。 当作品运行时,作者,审稿人和摄影师会被署名署名,从而提升了原本匿名的学术作品,并使读者可以识别参与该过程的每个人。
结果是同行评审比传统学术期刊更快,更友好。 批评者指责 混合教育学 过分舒适:约70%的接受率比其他期刊要慷慨得多,而且作者和审稿人之间的界限历来是多孔的(现在该期刊依赖主题论文征集了,所以有所减少) 。
我也分享其中的一些担忧,仅仅是因为我相信期刊需要这些界限来确保自身的可持续性。 但是我也相信那些批评没有 抓住 重点: 混合教育学 不是传统的学术期刊。 散文看起来更像是扩展的博客文章,而不是期刊文章:它们简短(通常与本专栏的长度有关),个人性和政治性。
朋友解释说:“我们一直在告诉作家,不,真的,说的意思是,不要对冲。”
当前的论文征集邀请将教育学政治化的论文。 最近的出版物批评了市场导向的教育,并提出了批判性的数字素养作为纠正错误信息的手段。
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Thomas) 成为批判性反思老师 和约翰·爱尔兰(John Ireland)特聘主席的作者斯蒂芬·布鲁克菲尔德(Stephen Brookfield)欢迎该杂志的党派关系。 他说:“我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游击党网站,旨在帮助教师与学生一起发现意识形态操纵,这是完全有前途的。”
威廉与玛丽学院副教授利兹·洛什(Liz Losh)补充说:“混合教学法在断言关键数字教学法的价值以及承认教育和技术都不能像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中立这一事实方面做得很好。” 学习战争:数字大学的发展之路》 。
该期刊的党派关系为其自身的学术资格提出了挑战。 虽然 混合教育学 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注册为同行评审期刊(通过Google Scholar快速搜索返回了数十篇文章),但许多机构都不愿意接受这些出版物以进行终身评审。 抵制通常与该期刊的数字形式和其党派关系密切相关。 该项目的共同创始人杰西·斯托梅尔(Jesse Stommel)写道,在他被劝告要“专注于面向学术受众的传统同行评审出版物”而不是面向公众的数字奖学金之后,他离开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今天,他担任玛丽华盛顿大学教学技术部的执行主任。
该杂志在学术信誉方面的损失使它在公众知名度方面得到了提高。 朋友说,该网站平均每月有10, 000至15, 000位读者,对于有关关键数字教育学的期刊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小。
网络文本期刊《 开罗:修辞学,技术和教育学 期刊》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谢里尔·鲍尔(Cheryl Ball)对该期刊的定位进行了描述:
“当我想发表要比其他任何在线开放获取期刊更广泛的 报道 时,我都会去研究 混合教育学 。要点。”
对话在哪里继续
数字教育学实验室通过一系列外展工作扩大了该期刊的影响范围。 在项目的早期,领导者尝试了大规模的在线公开课程(MOOC),他们最初通过Instructure Canvas,然后通过Twitter进行了授课。 与许多MOOCS追求规模而追求规模不同,DPL的开放课程是超关键的。
“我想,如果要进行MOOC,就必须是关于MOOC的MOOC。因此就叫MOOC MOOC,” Middlebury College DPL主任兼教学设计师Sean Michael Morris解释说。 “重点是要检查什么是MOOC。作为下一轮教育的发展,人们对这件事值得赞赏吗?融入其中是什么感觉?”
除了作为教学活动外,MOOC制作还吸引了新的人才进入DPL轨道。 朋友说他是通过MOOC MOOC参与的,而其他许多人则是通过Twitter上的#digted聊天参与的。
同时,Friend使用播客扩展了始于期刊 Hybrid Pedagogy 的对话。 现在是第十二集,播客的叙事性和对话性比期刊上的要多。 Friend解释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使用播客来围绕文章进行对话。”
斯图梅尔观察到:“学者们经常写文章,发表文章,然后继续做其他工作,而不是在思考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什么,叙述与下一篇文章之间的痕迹是什么。” “这些播客成为了面包屑足迹的一部分。”
也许最重要的对话空间是面对面的地面数字教育实验室研究所。 这些为期五天的研究所在开罗和爱德华王子岛的不同地点提供服务,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交流,讨论教学方法以及尝试新工具和方法的机会。 如果该期刊是关键数字教育学院,那么该研究所就是夏令营。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娱乐和游戏。
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莫里斯解释说:“许多学术界人士不习惯谈论教学法,他们也不习惯以批判的方式考虑自己的教学。” “这么多的教学都是自主的,这与像这样的社区完全不同,在社区中,每个人都将其摆在桌面上。”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该研究所仍在继续发展。 首届于2015年举办,吸引了75名参与者。 今年夏天,组织者预计将有一百多人参加玛丽华盛顿大学的一所学院,另外还将有75家将在温哥华开设的第二所学院(以适应受美国移民禁令影响的人)。
迈向可持续发展
迄今为止,该研究所已通过注册费和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资助。 (DPL通常会获得补充的会议空间和折扣餐饮。)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所的领导者会放弃酬金,以便为参与者提供奖学金。 但这只是研究所。 当您考虑编辑文章,制作播客和维护社交媒体生态系统所需的所有工作时,您意识到该机构无法补贴DPL的其余部分。 恰恰相反,董事们是在与其他学术职责同时进行这项工作的,不幸的是,这在大学中并不罕见。
DPL与其他学术初创公司不同,因为DPL与机构没有关联。 最初,这种选择具有战略意义,但如今,缺乏从属关系给该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洛什说:“教育技术-甚至免费和开源资源-都需要劳动力,技术人员的时间和编程人员。” “玛丽·华盛顿大学曾经是“一个人的领域”的领导者,它通过举办许多数字教育学实验室活动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它们可能没有继续国际扩张所需的资源。”
实验室的领导了解这一挑战。 Stommel解释说:“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选择不加入机构,因此只有非常特殊的机构才能与Digital Pedagogy Lab和 Hybrid Pedagogy 建立关系。” “我希望数字教育学实验室能走出屋子去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