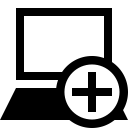目录:
视频: ä¸è¦å²ç¬æåçæ§ (十一月 2024)

在15岁左右时,我开始经历周期性的灼痛,从腿的外侧向下穿过,并穿过肩blade骨逐渐向上。 疼痛有时会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我被迫with着拐杖走路,几乎无法管理楼梯。 一次失眠几个月,我整天都会and行和做鬼脸。 最糟糕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医生无法诊断问题,我辞职了,要尽最大努力。
一旦打到30多岁,我就受不了了,决定要做些什么。 我要求自己继续看医生,直到 有人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经过一系列专家的研究后,我最终找到了一名风湿病医生,他诊断出我患有炎症性疾病,这在科学上还没有完全被完全理解,称为 强直性脊柱炎 (听起来像咒语)。
现在,可以通过特殊饮食来治疗这种情况(请不要给我发送有关该主题的任何信息,我知道),但是食物限制非常严格,因此我的情况并不总是一致的。 但事实证明,现代科学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法。
我的风湿病学家建议我开始一种药物疗法,这种药物被称为生物药物(有时也称为“生物药物”),可以直接从活生物体中渗出。 我对科学技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能力深信不疑,因此我很乐意看到这种尖端疗法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很高兴地说,大约一个月后,这些治疗方法奏效了-实际上,它们的效果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几乎完全没有痛苦,甚至开始跑步。 (我应该注意,我所用的药物带有一些严重的潜在副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会降低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抵抗某些癌症的能力。就我而言,权衡是值得的。)
现在,这种药物与我服用过的其他药物不同,我必须注射。 大多数用于抵抗炎症的第二代生物制剂必须通过注射器或静脉注射直接引入体内。 我必须学习使用像一次性器具这样的一次性易燃笔,并将其保存在冰箱中。 有一个学习曲线,但不是一个尖锐的曲线(这肯定有助于我在针灸方面一点也不怯que)。
那么,我向体内注入的这种神奇的树胶是什么? 它来自自然资源,但与此同时,它实际上并不自然。
魔术师
科学家一直以来都从生物体内获取药物,几乎您所服用的每种疫苗都可以被视为生物制剂。 但是,近年来,随着基因操纵技术的出现,这些药物的范围迅速扩大。
尽管“生物”的确切定义因监管机构而异,但如今该术语通常用于指代通过在基本遗传水平上调节细胞以将其转变为活体工厂的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药物。
根据FDA自己的描述,“与大多数化学合成且结构已知的药物相反,大多数生物制剂是不易识别或表征的复杂混合物。” 许多第二代生物制剂(与疫苗等第一代生物制剂相反,在过去15年左右出现的生物制剂)是人类无法再生的。 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 但是,科学家们可以使用现代的遗传操作技术来哄动活细胞培养物来做到这一点。 其中有一个生物学故事的皱纹-它们可能非常昂贵。
这些药物的生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工业规模上。 不仅存在先进的基因操纵方法,而且细胞培养特别容易受到污染,必须在非常无菌且温度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进行维护,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训练有素的工人的监督下进行。 当您认为患者人数相对较少时,价格必然会上涨。
为什么我们要回答愚蠢的问题
我只能自言自语,说这些药真是天赐之物,确实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 但是我也很着迷(甚至谦虚)考虑如果没有经过数十年的科学询问就无法进行这种治疗。
直到达尔文,孟德尔和屈臣氏(Watson&Crick)团队一直沿用的科学历史路线,都不知道有一天它将帮助一位中年科技博客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减轻痛苦。 他们都只是想知道奇怪和不切实际的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政客们想要在科学研究的支持下平衡预算时感到恼火的原因。 尽管有多种方法可以最佳地利用研究经费,但它们的好处却是无价的-并非总是立即产生的(量子物理学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在智能手机的功能中找到用途,因为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卫星配置中花费了多年时间)。
我们无法预测今天不切实际的研究将如何影响一些重大突破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的税金能够资助对诸如“引力子是否存在?”,“冥王星看起来像什么?”或“整个宇宙是全息图?”之类的不必要的疑问的调查。 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新突破-实际上,它们可能不会。 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将有一天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