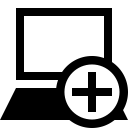目录:
视频: 搗蛋!宝蓝萬聖節糖果玩具〜 (十一月 2024)

大多数时候,我梦想着将iPhone 7甩下悬崖。 我想象这块750美元的平板在空中飞舞,跳过了动荡的海洋表面,沉入了深深的黑暗深处。 当这种方法不起作用时,我想象将其从窗户上落下来,看着屏幕在人行道上破碎,一千条发际线像闪电一样在其光滑的表面上弯曲成锯齿状。

令人惊讶,我知道。 千禧一代被认为是无法忍受的,会自拍的社交媒体上瘾者,每次Wi-Fi中断时都会哭泣。 你知道类型。 我们的鼻子几乎粘在屏幕上。 我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根据绝大多数千禧一代的思想作品,我们为短暂的喜欢,模因和鳄梨吐司而生。
事实是,我想念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 但这不是因为我是技术恐惧症。 我喜欢我可以和日本的朋友一起玩围棋游戏,或者醒来加州老同学的Facebook Messenger文章,内容是关于亚当·德鲁(Adam Driver)在 《最后的绝地》 ( The Last Jedi)中 生猛的家伙。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不用花任何钱就可以打开KakaoTalk并给我在韩国的父亲打电话。
但另一方面,现在几乎不可能从心理上注销。 在过去的48小时内,我收到了来自应用程序,社交媒体,文本,聊天,通话,电子邮件,Slacks和提醒的400多个通知。 从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在Instagram上跟随我到我的机器人吸尘器,一切都提醒我它再次被卡在电线上。 一次,我在半夜醒来,因为“如果那么那么(IFTTT)”决定用78条通知炸毁我的手机-它真的很想让我知道它已经备份了我的“发现每周”中的所有照片和曲目Spotify播放列表。

当然,我可以关闭这些警报。 或自定义它们,这样我就只能得到某些。 相信我,我已经做到了。 不幸的是,这也是我的工作中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设备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查看应用程序的推送通知的工作情况或智能手表接收文本的速度。 因此,这意味着所有内容至少响起两次嗡嗡声:一次在我的手机上,一次在我正在测试的许多可穿戴设备上。
这是引发焦虑的噩梦,旨在确保我再也不会专注于任何事情。 我将坐在办公桌前或电影院里,难免会感到全身的振动越来越多。 它从手机放在口袋里开始,一直到我的手腕和手臂。 有几天,我感到嗡嗡声,没有声音。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如果我只让我的手机和可穿戴设备形象地和字面地嗡嗡作响,那将是完全可以的。 警报可能是我一段时间未使用的应用程序,像前恋人一样提醒我它仍然存在,也许我应该回来(不)。 或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短信中充满了GIF,模因和存在的焦虑,这些焦虑使为什么那个可爱的男孩或女孩不会发短信。
但是也有1%的机会实际上很重要。 就像当我堂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爷爷去世或对时间敏感的工作Slack一样。 关键是,您实际上从来不知道,因此您沉迷于确保它不是必需的。
您会感到惊讶的是,每次嗡嗡声,您失去手机的时间。 当我向外界开放的唯一窗口是古老的56K拨号音时,很容易将精力集中在与互联网无关的活动上。 有限的连接令人欣慰。 我从不怀疑克拉伦登或梅菲尔是否适合我平庸的一餐。 我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朋友在做什么的证据,甚至可能没有我。 如果我很迷恋,我就不必在镜子前给自己鼓舞人心的讲话,避免像轻度无助的精神病患者那样在社交媒体上缠扰他们的每一个醒来的决定。 只需一声嗡嗡声即可中断您的流程。 一条通知将您冲洗到网上兔子洞。

一旦您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您一直在忙,就祝他们好运。 突然,这是深夜,您正在安慰您的年迈的父亲,不,您没有体重增加,是的,纽约和韩国之间的时差意味着不建议在凌晨3点拨打30分钟平日。
足以让我想从Maxine Waters上浏览一下,并腾出我的时间。 但是,我非常站不住脚的解决方案是一次连续虚假几天。 我将所有可穿戴设备丢进抽屉,然后将手机埋在我听不见嗡嗡声的地方。
那第一个小时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瘾君子。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错过了重要的事情-剧透,我没有。 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开始解放了,就像记得如何呼吸一样。 事实是,当我回来时,所有那些模因和文字都将在那里。
而且我会(总是)回来。
我,智能手机成瘾者
两个星期前,我在苏 活区 的安吉丽卡电影中心观看了深夜的 Tonya 电影。 经过四分之三的时间,一个疯狂的人认为闯入我的剧院挥舞着吉他盒是一个好主意。 有人喊“枪!” 随后发生踩踏事件。
除了我的生活,我最关心储蓄的还是我那笨拙的iPhone。 当我在过道里挣扎时-心跳加速,并确定我会死于后背的子弹-我知道我的手机是我的生命线。 如果我活着,我需要它来找到我的朋友,并让家人知道我还不错。 如果我有手机,可以用它打电话给Lyft,然后把它放回家。
在迷恋中,我丢下了外套,包和鞋子,但没有丢掉手机,直到惊慌失措的电影迷把我撞倒了。 此刻是模糊的,但我确实记得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握住手机。 我放开了它,精神上把它放到了哪里,以便我生存下来时能够找到它。 太疯狂了
并没有让我迷失,只有当我放下手机时,我才能将自己抬起身来并跑到安全地带。 我狂奔着离开那家剧院,赤脚跑了两个街区,进入了寒冷的十二月夜。 我只是停止跑步,因为我意识到我的朋友们找不到我。 没有电话,我无法乘车或让任何人知道我还好。
原来那晚没有真正的威胁。 只是一个疯狂的人像老式的黑手党成员在吉他盒周围挥舞。 一旦我知道了,第一要务就是找到我的手机。 不仅如此,我可以回家找到朋友,而且因为我的整个生命都在那里。 我的银行信息。 我的工作和个人电子邮件。 我的朋友和家人的联系信息。 我可怕的情绪诗。 任何拥有它的人都可以访问有关我的所有信息。 我认为直到真正放回手中之前,我才真正放松。
我不知道这对我,你或整个社会有何影响。 我所知道的是,我陷入了需要(但讨厌)我的智能手机的精疲力竭的过山车,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下车。